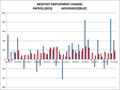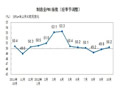2012年,“欧债危机毁灭全球经济”的预言会成为现实吗?
从中东欧、冰岛和迪拜,到千疮百孔的希腊,再到欲说还休的其他欧猪国家(PIIGS国家,分别代表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再到举足轻重的美国和法国,债务危机席卷全球,主权评级调降间,危机波折恶化引致处处硝烟,在“警报—博弈—救助—新警报—新争议—新危机”的恶性循环中,全球正经历着近似2008年、远似1929年的痛苦折磨。
虽然当下的凄凄惨惨戚戚让市场心存忐忑,甚至联想到末日般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崩溃,但纵观历史,全球经济从未因为主权债务危机而停止呼吸。
根据IMF的数据,1824~2004的180年间,全球陆续发生过257 次主权债务违约,此间只有1929~1933年的大萧条给全球经济留下了永久疤痕,而源于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大萧条与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太大关联;1981~1990年的十年是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最为频繁的十年,共发生过74次主权违约,但此间全球经济并未经历伤筋动骨的挫折,并实现了3.3319%的年均增长,增长水平甚至超过了随后一个十年3.1991%的年均增长。
那么,2012年到底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还需理性解析数据,并在逻辑推演中展现一个更为可信的2012债务危机影像。
2012:还是债务危机年
从表面上看,2012年依旧是一个债务危机年,但似乎并不会比2011年更糟。
利用IMF、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估算,2012年,全球的公共债务预估值将为59.025万亿美元,较2011年的55.726万亿美元增长5.92%。按照2012年各国GDP的预估值,59万亿美元可以买下3.8个美国,或7.62个中国;按照2012年全球GDP的预估值,59万亿美元甚至可以买下五分之四个地球。因此,就绝对水平而言,2012年债务负担依旧是全球不可承受之重。
就结构而言,全球沉重的债务负担很大程度上源自富裕集团对资金的渴求。2012年,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预估值为49.614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预估值的84.05%,这一比例甚至较债务危机高峰年的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上升了1.1和0.45个百分点。但就相对水平而言,2012年的债务危机还不具有一剑封喉的爆发力。2012年,全球公共债务增长率预估值仅为5.92%,不仅低于2010年14.29%和2011年11.77%的增速,还低于过去十年10.04%的平均增速。
从深层次看,2012年的债务危机却并非如表面那么简单,规模增速下降的债务危机由于复杂的风险蕴藏,而显得与众不同。2012年的宏观水土已与过去大相径庭,而这正是放大债务危机风险、孕育金融风暴,甚至催生经济灾难的温床。
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叠加
首先,2012年的债务危机伴随着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的相互叠加。
一方面,对于负债国而言,短期风险主要体现在偿债压力加大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突然增加的到期债务可能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人无奈的是,2012年依旧是一个高压年,大量到期的公共债务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不断吞噬着紧巴巴的市场流动性和紧绷的市场信心。根据Bloomberg的统计,在2011~2020年的十年里,2011~2012年是偿债高峰期,而2012年更是偿债压力最大一年。
另一方面,对于负债国而言,长期风险主要体现在清偿能力缺失导致的违约风险,简单地说,就是资不抵债引发技术性破产。
2012年,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2个国家中,有44个国家债务率预估值高于60%警戒线,有12个国家负债率预估值高于100%的技术破产线,占比分别高达24.17%和6.59%。这12个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经济体按负债率预估值由高到低分别有日本、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美国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不仅简单共存,甚至会相互牵制、相互叠加:化解短期风险需要政府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到期债务偿还,势必减小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能空间,进而削弱偿债能力,加大长期风险;而化解长期风险则需要政府开源节流,推出令人信服的财政巩固方案,而这种节衣缩食应对长冬的举动又会减少当期还款的可用资金,进而加大短期风险。总之,长短期风险相互叠加是2012年我们将要面对的危机特征。
金融困境与财政困境交错
其次,2012年的债务危机伴随着金融困境和财政困境的犬牙交错。
一方面,金融困境体现为风险“三重门”:
其一,银行业恐将再受重创。
次贷危机留下的伤口并未完全愈合,持续恶化的债务危机又一次撕裂了未愈合完全的伤口。根据BIS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全球银行(主要是欧洲的银行)持有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公共债务的占比分别高达54.4%、20.26%、19.37%、25.21%、24.03%和52.11%,较高的债务风险敞口让银行业特别是欧洲银行业步履蹒跚。
欧洲央行的压力测试显示,若债务风险持续扩散,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足8%的银行将达到53家,资金缺口1017.1亿欧元;高盛研究团队的研究则显示,如考虑债务风险,核心资本不足的欧洲银行将达27家,资金缺口298亿欧元;IMF则估计,债务危机将给欧洲银行业带来高达2000亿欧元的可能损失。
其二,债务货币化倾向推高通胀预期。对于政府而言,理论上永远存在一劳永逸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即发行货币征收通胀税。真正的风险其实并不在于政府会不会这样去做,而在于只要市场认为债务危机的持续恶化将加大这种可能,那么通胀预期就会上升,进而给实际物价稳定带来冲击。
其三,危机恐慌引发市场动荡。沸沸扬扬的债务危机让2011年的国际金融市场陷入一波三折的巨幅波动之中,而潜伏于2012年的更大、更多、更复杂的不确定性,恐将在国际金融市场搅起更大的惊涛骇浪。
另一方面,财政困境体现为赤字“全球化”的延续。经历过2011年债务危机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肆虐,欧美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高支出状态,学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各国陆续明确了涉及未来的财政巩固计划。
尽管欧美国家的“节流”之举值得称道,但未必会带来透支风险下降的结果,关键在于,经过2008~2011连续4年、两种危机的接连摧残,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已有所下降。经济学家罗格夫研究了44个国家200年的债务历史,得出的结论显示,当负债率从60%~90%区间上升至90%以上区间时,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从2.5%降至-0.2%。而自2008年至2012年,全球负债率上升了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可能已经受到1个百分点左右的债务危机冲击。
钱永远是赚出来的,而非省出来的。“节流”与“缩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能是2012年财政困境和赤字全球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