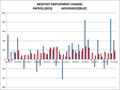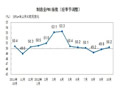自去年6月底审计署披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后,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得到空前重视。一方面,通过展期旧债、控制新债,确保不发生偿债危机的“黑天鹅”事件;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地方三级财政收入(本级财政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净收益)来应对到期债务本息的偿还。最近两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全面超过债务增速,收支重新回到相匹配的轨道,债务杠杆率也回到100%以下的安全水平。特别是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达到了30%,而新增债务则零增长,地方债务风险进入“软着陆”的安全通道。
事实上,这种应对地方债务压力的策略是合理的。一方面控制新增债务的产生。尽管地方政府投资基本上集中在市政建设、道路交通和民生领域(保障房、农林水利),带有弥补短板和历史欠账的特征,但2009年以来这些领域的投资基本以对冲经济下滑为目的,重视规模而忽视了效率,超前和泡沫化很严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无效投资。控制新增债务阻止了投资过剩继续膨胀,为解决存量债务赢得了空间。另一方面纠正存量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地方投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项目现金流回收是长期的,需要通过展期和借新还旧来人为拉长偿债期限,才能依靠经济增长和财力恢复来逐步消化债务。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业界和学术界的观点较为一致: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价格控制能力,容易制造出新市场和腾挪产能过剩的空间。再考虑到近年来强大的财政实力(2011年地方政府未偿债务余额仅占地方财政收入的85%)和上级转移支付能力,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很小。
稳增长再度推升债务风险
但是,地方债务风险“软着陆”态势今年以来似乎出现转向的苗头。3月底以来发改委不仅放行了一批搁置在审批环节的地方基建项目,而且加快了新增项目的审批进度,而为了配合稳增长,近期有13个省市发布了“十二五”期间总额达13万亿的投资计划。
在民间投资不振情况下,出于反周期需要启动政府投资,但政府应当着力于创建民间投资、消费的大环境,如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障碍、减税以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增加民间投资和消费的补贴等。很长时间来,基础、道路和市政设施一直是我们的短板,每逢经济遭遇挫折(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和2008年金融海啸),便拿基建、道路和市政设施建设来缓冲。早期这类投资效率很高,对于我国出口和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很强,但经过15年的飞速建设,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大干快上”,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早已饱和,加上屡次充当救火工具的角色,重短期规模不重长期效率,投资回报率和社会效益不高。
在稳增长优先旗号下,本轮地方政府投资潮的出现将2010年以来中央为控制债务风险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财经纪律束之高阁。地方政府会借这一机会最大化自己的债务,使得本来就混乱的地方债务将更加混乱,地方政府会将最大化债务的机会主义风险、投资失误的决策风险完全转嫁给中央政府,导致中央政府信用不得不成为债务的最后贷款人和追加补助人。这也是为什么本轮地方政府投资潮中,上述多数省市的计划投资额远远大于其去年财政收入的主要原因了(如天津、长沙、贵州的投资额分别是去年财政收入的2.6倍、2.5倍和2.3倍),不考虑收入的盲目开支倾向可见一斑。
近两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急剧膨胀,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地方三项收入(本级财政、中央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净收益)达到创纪录的12.55万亿,这使得地方债务问题显得容易对付。但是,这只是站在地方显性债务的角度考虑的。中央政府作为债务风险的最后承担人,目前我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70%以上,与世界主要国家基本差不多(低于日本和美国)。但是,当前我国公共债务计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计入高校债务、城投债、政府性实体的信托融资和以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二是没有计入国土整治、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其他隐性负债。上述两类债务在发达国家基本不存在,因而我国公共债务存在被低估的倾向。由于社保缺口和其他隐性债务难以准确测算,公共债务到底被低估了多少还不清楚,但基于审慎和保守估计的原则,形势不容乐观。
未来,我国公共债务面临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在经济社会转型压力下,上述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社保债务偿还、高房价下的住房保障、贫富差距扩大下的社会维稳债务;二是2008年底扩大内需以来,投资快速扩张下产能过剩所导致的硬性债务,如对过剩行业和国企的补贴、解决三角债的补贴支出、解决银行风险的补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