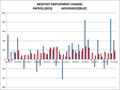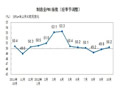美联储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量化宽松(QE)结束的触发条件是失业率降至6.5%,因此,很多人将目光牢牢地盯住失业率和非农就业等数据上。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量化宽松退出与否、何时退出,不能完全根据单一的失业率数据,更可能的情况是,美联储会根据多种复杂因素进行相机决策。
美国政治视角
持续了4年的量化宽松,招致了方方面面的批评,其中火力最凶猛的要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美国国会内的部分共和党人士。奥地利学派学者指出,货币宽松和对金融业的定向救助是中央银行指挥的一场的“计划经济”,大量潜在的僵尸银行和有毒资产并未得到市场清算,经济资源错配难以得到纠正。在没有经历创造性毁灭的情况下,经济结构难有实质性改革。事实如此,近几年美国经济结构未根本触动,吸纳就业的制造业和中小企业起色不大,而依赖政府救助的金融业还在赚取大量利润。
从政治上看,为大量国债进行融资的QE也是在践行“政治正确”。近年来美国政治理念整体左转,少数族裔在政治上的崛起——而他们更依赖一个依靠不断举债、给社保注入资金的大政府,没有太多兴趣在一个小政府模式下进行清教徒式的个人创业。但是,这一套模式会导致政治对立不断升温。正因为如此,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声称要撤换伯南克。“占领华尔街运动”、崛起的茶党、大选后共和党州掀起的独立运动,均说明维持量化宽松的政治代价,美国正在被分裂为两个美国、两类人群:一群人依赖于欧洲式的大政府支撑,而另一群人则相信美国梦是依靠个人奋斗。后者对量化宽松持反对态度,希望尽快消除量宽依赖症、推动企业家精神发展。而这种政治环境,是伯南克及其继任者必须加以考虑的。
财富效应视角
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是私人消费和投资。财富效应对促进投资和消费很重要。去年9月美联储购买MBS债券以及随后购买长期国债,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财富效应。
数据表明,第三轮量化宽松后两个多月内,美联储持有的MBS规模未见增长,但11月底出现实质性上升。至今年3月底攀升至1.08万亿美元,每月多扩张的100亿美元可能是用其他资产置换而来。这样,在2月底30年期抵押债券利率降至历史新低附近。这给MBS发债机构和地产商一个利好信号,使其增加融资规模,扩大投资,推动美国房地产产业链的复苏。同时,去年10月份日元开始出现贬值趋势,加之人民币升值,重新催生了以新兴市场为导向的日元套利资本泛滥。今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欧元区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对冲基金削减大宗商品的风险敞口,致使大量套利资本回撤,流入美国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正如美联储官员费舍尔声称,美国股市上涨是美联储对货币政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股市和房地产之间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效应。股市上涨将激发握有大量现金的美国企业掀起新的大规模投资;从房地产来看,如果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则可以解套大量负资产家庭。房地产和股市形成的财富效应可以推升消费的增加。
因此,联储对MBS债券的“特殊照顾”会让美国房地产市场投资获得无风险收益,从而吸引全球资本流入。财富效应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产生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影响,也影响着量化宽松退出的时机。
全球经济再平衡视角
目前,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可能快于预期,这对推行量化宽松的伯南克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对于美国来说,今年将大幅削减国防、教育等开支,促进双赤字长期减赤目标,不过其时间节奏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中国投资的削减和影子银行问题都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从而让人民币上涨趋势不再,甚至日元大幅贬值会潜在地增加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这样,如果人民币不能继续升值,美联储实施廉价美元的战略空间就大大削减,导致量宽无法延续。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三次量化宽松的前后,中国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人民币也出现了升值趋势。
关于量化宽松的三个新的观察角度中,某些因素是相互抵触的。例如,日元贬值将对人民币和其他货币构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从而使与汇率走势同向的资产价格出现下行风险,但这也能促进资金流向美国,推动美股繁荣,强化财富效应;只要中国经济的明斯基时刻尚未真正到来,人民币总体贬值趋势未形成,美联储就还有空间继续印钱;同时,随着去杠杆的初步完成,必须妥善退出以释放企业家精神推动下的美国内生增长空间。
因此,伯南克和美国政府的总体策略很可能是,在这一切潜在动荡因素之间走钢丝,不断协调平衡各种不稳定性,争取时间和资本确保美国经济平稳回升。至于6.5%的失业率政策目标,则可能只是根据核心通胀率从菲利普斯曲线中推导出来的一个假定值,正如美联储今年1月议息会议决议所暗示的,失业率目标并非是退出的一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