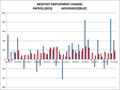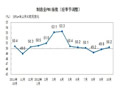今年是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以来的第八年,而上一次可与次贷危机相提并论的大萧条,起始于1929年,1929之后的第八年是1937年,那一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从复苏周期再次掉入衰退周期。再看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尽显疲态,除了层出不穷的黑天鹅,几乎看不到兴奋点。几乎可以确定,这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启动后最黯淡无光、令人失望的一年。对此,我国更需保持警醒,将底线思维、强国思维、金融思维贯彻到底。
程 实
历史从不简单重复,可危机却总是有太多相似之处,人性使然。今年是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以来的第八年,而上一次可与次贷危机相提并论的大萧条,起始于1929年,1929之后的第八年是1937年,那一年,美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从复苏周期再次掉入衰退周期。再看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尽显疲态,几乎从任何一个角落传来的信息都带着虚弱的味道。美国经济开局就遇到了季度负增长,欧洲经济一体化再受希腊危机重创,日本陷入比失落十年还沉闷的经济困局,新兴市场经济普遍萧瑟,大宗商品市场一片死寂,股市在间歇性狂躁之后呈现出全局性颓势。除了层出不穷的黑天鹅,全球经济几乎看不到兴奋点。几乎可以确定,2015年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启动后最黯淡无光、令人失望的一年。
在我看来,这也是种必然,全球经济不过重新体验了1937的心路历程.此时恰处于危机对实体经济深层影响全面显现、而短期刺激政策又捉襟见肘之时,旧力已尽,新力未生,经济发展无枝可依。虽然科技始终在加速发展并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根本支撑,但其他要素的拖累正在大幅抵消科技的贡献,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正处于增速大幅放缓、甚至绝对停滞的羸弱状态。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抑制的原因主要有六个:其一,全球化大幅放缓。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深度重组的过程,是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的根本保障。但今年以来,全球化放缓的态势深度加剧,国际贸易增长乏力,跨境经济金融互动减弱,保护主义渐成潮流。更令人忧虑的是,今年起出现了罕见的反常现象,多国本币大幅贬值,出口却未见增长,甚至大幅下降,这让竞争性贬值陷入无用却流行的境地,给全球经济徒增发展烦恼,并引致全局利益和个体利益双输的尴尬格局。
其二,新生发展亮点黯然失色。新要素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是全要素生产力不断提升的时代内涵。但2015年以来,新要素并未给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预期中的贡献。一方面,新兴市场陷入全局性困境,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和巴西陷入衰退,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也低于预期,在经济失速的同时,新兴市场普遍面临强势美元的挑战,资本外流,外储缩水。另一方面,新产业革命并未掀起巨浪,由于保护主义政策将重心放在传统行业,刺激措施很难顾及新兴行业,全球产业变革实质推进弱于预期。
其三,金融深化作用潜在削弱。今年以来,无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面临着风险加大、渠道收窄、创新乏力的挑战。国际金融市场巨幅波动,不仅未能充分发挥支持并引领实体经济稳健复苏的作用,反而成为系统性风险滋生的温床。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环境恶化,投机氛围浓厚,部分市场还形成了需求萎缩和市场下行的恶性循环。
其四,人力资本提升明显不足。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支柱。但2015年以来,人力资本增长乏力愈发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人口大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下降并消失,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二是全球人口质量提升速度放缓,全球经济颓势不仅降低了贫穷国家年轻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还对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就业带来巨大冲击,阶级固化愈发严重,年轻人获得素质提升的机会在普遍减少;三是人的信心在削弱,各类指标显示,金融危机及其引致的地缘政治动荡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全球民众对经济增长和政策调控的信心在普遍下降,这实际上通过拉低长期消费倾向和长期投资预期而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冲击。
其五,经济发展信仰受到冲击。现代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斯密市场经济理论基石上的宏伟大厦,人们对经济内生增长的信仰决定了要素投入的可能回报。但今年以来,一个不易察觉的态势是,全社会的经济信仰在逐渐动摇,人们越来越怀疑内生均衡的自我实现能力,越来越担心市场在自我修复中突然死亡的可能性。如此背景下,强调政府调控的新凯恩斯主义开始成为主流,媒体也开始热议MIT(麻省理工学院)学派在全球货币政策决策层的主导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日渐式微。这种信仰的动摇实际上削弱了微观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感和自信心,对经济长期内生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六,不确定性在上升中钝化。今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地缘政治博弈愈发复杂,全球利益争夺愈发激烈,经济金融波动性显著上升。比不确定性上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警惕在逐渐变得迟钝,这不仅刺激了不确定性的自我衍生,也反映了全球经济风险管理的疲态,进而给风险大量积聚后的突然集中爆发埋下了伏笔。
可以想见,全球潜在增长的增速放缓或绝对停滞正在悄然发挥威力,如此背景下,政策对这一态势的对冲能力却在显著下降。全球范围的政策搭配格局都陷入了类似的尴尬:扩张性财政政策遭遇债务瓶颈,各国政府几乎都缺少主动加杠杆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宽松货币政策余力渐失,全球利率水平已到绝对低位,通胀压力开始显现,货币政策对刺激增长有心无力;竞争性汇率政策无效对抗,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刺激效应大范围消失,总需求萎缩让汇率博弈变成鸡肋;结构性政策广泛缺位,增长压力之下,结构调整愈发困难。两相作用,潜在增长动力的缺失无法得到政策之力的有效抵补,全球经济很难避免全局性困境。
对于我国而言,在“1937魔咒”笼罩全球经济之时,更需保持警醒,将底线思维、强国思维、金融思维贯彻到底。既要防范外部环境恶化对我国经济的意外冲击,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夯实并挖掘中国长期增长潜力,又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在全球大环境中的定位,虽然在沪深股市大幅震荡背景下唱空中国的声音不断增大,但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底气相对而言还很强,需引领全社会增强信心;更应在国际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用好、用活金融手段,防范金融风险,稳住金融进而稳住中国经济。